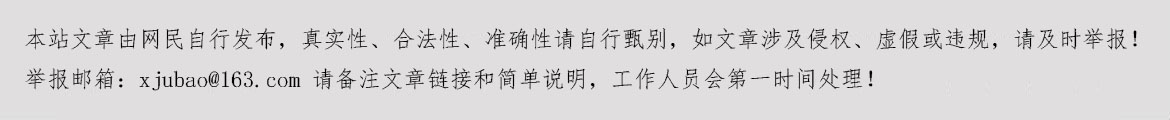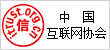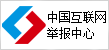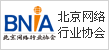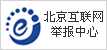今天全国卷高考的《大观园试才题对额》 我写过一篇肯定0分的作文
2022-08-30 20:35:02
一起看电影网免费在线看最新电视剧 https://www.yiqikan.org
全国卷高考,问了《大观园试才题对额》那事。
我几年前写过个别样想法,有些同学估计读过这篇了。
当然如果考场写出来,肯定是0分作文:
那一回,本身是借着贾政贾宝玉和清客们共同上演的家庭喜剧,顺手介绍了大观园。
然而(然而意味着唱反调):
这出喜剧的过程,极体现传统家庭中,亲子关系别扭的一面。
这故事的公式,读过的都一目了然:
政老爷其实挺喜欢宝玉,只是,政老爷对贾宝玉的爱,都是绕着弯子来。
政老爷见了宝玉,有事没事,一定要训,这样显得他是严父。
妙在他得当着人训,其他在场清客们,就负责劝说。
宝玉再一卖萌,这事就过去了。
那场游园题联,贾政每每等清客们说完了,再征求宝玉的意见。原文说得很明白:
“原来众客心中早知贾政要试宝玉的功业进益何如,只将些俗套来敷衍。宝玉亦料定此意。”
就是父子和清客一起演严父孝子戏罢了。
——要不然,养清客干嘛?就是看眼色识趣,给你下台解围用的。
宝玉说了“曲径通幽”,清客们一通夸,政老爷就说:
“不可谬奖。他年小,不过以一知充十知用,取笑罢了。再俟选拟。”
——不错不错,也算说得出道道了。
宝玉说出“沁芳”,政老爷拈髯点头不语:那是政老爷很高兴。
政老爷对宝玉说:
“今日任你狂为乱道,先设议论来,然后方许你作。”
——你就放心说吧,只是要先点评了再说,别让大家觉得你理论根底差。
贾宝玉说了一个,贾政点头道:“畜生,畜生,可谓‘管窥蠡测’矣——再题一联来。”
——小东西说得不错,有见识,还不接着再来一联?
贾宝玉大肆议论一番后,贾政一定得装生气:“叉出去!”
刚出去,又喝命:“回来!”命再题一联:“若不通,一并打嘴!”
——“刚出去,又喝命”,这气啊,都是生给清客们看的。
等贾政要征求贾宝玉意见?自然也不会好声好气,一定要喝:
“怎么你应说话时又不说了?还要等人请教你不成!”
——如果说成“宝玉,你来说一个?”之前绷起来的脸面就没了。
所以了,政老爷都只是对宝玉表面凶凶罢了。宝玉其实也知道,所以虽然被政老爷骂,还是经常多嘴多舌。
也就是清客们辛苦,看父子秀恩爱,还要假装劝。
像极了现在看小两口吵架还得假装劝分劝和出主意的闺蜜——回头一看,人又好了!
当然这父子俩,也有稍微真情流露的时刻。
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将终时,宝玉做长诗。贾政让贾宝玉口占诗,自己亲自誊写。这段原句温馨得很:
——向宝玉笑道:“如此,你念我写。不好了,我捶你那肉。谁许你先大言不惭了!”
等宝玉吟了几句,贾政道:
“这一句不好。已写过‘口舌香’‘娇难举’,何必又如此。这是力量不加,故又用这些堆砌货来搪塞。”
宝玉笑道:“长歌也须得要些词藻点缀点缀,不然便觉萧索。
——这两句已经是理论探讨了,旁若无人。
等宝玉吟完了诗,贾政的反应是笑:“虽然说了几句,到底不大恳切——去罢。”
——其实算是连笑带夸了。
这几段对话,在公开场合当着众人,已经算是旁若无人了。一对父子,心有灵犀,认真论诗呢。
贾政从来不乐意流露出当年自己吟风弄月的调子来,连点评都是一两句话的事。这时候却评断好不好、力量不够、堆砌,那是用了心在点了。宝玉也知道,所以说话越发放肆:说长歌要点缀这句,口气甚大,平时是不敢的。
只是,政老爷每一句赞美,定然是绕着弯说的。
这就说来话长了。
传统读书人交接,累得很,讲究说话要委婉,要给人台阶。
《围城》里,范小姐要勾引赵辛楣,拿剧本说事。辛楣出于礼貌,只好显殷勤,说要借看。
范小姐便撒娇:
“他们那些剧作家无聊得很,在送给我的书上胡写了些东西,不能给你看——当然,给你看也没有关系。”
于是这么一来,辛楣有责任说非看不可了。
所谓有责任,就是男士的礼节了。
如果这时候,硬邦邦来一句,“那我不看了”,大家都下不来台。
《倾城之恋》里,范柳原当着众人,忽然拉了白流苏,要带白流苏走人。“流苏没提防他有这一着,一时想不起怎样对付,又不愿意得罪了他。因为交情还不够深,没有到吵嘴的程度”。
——得交情深了,才能吵嘴呢。以前的上流人情,便是得如此委婉。
仿佛过年去做客,家里的熊孩子弄坏亲戚家东西了,不讲礼的人家会梗着脖子,护着孩子,觉得自己理不亏,“这才多少钱,小孩子嘛!”
有规矩的人家会走另一个极端,朝孩子发火,
“你这孩子怎么恁不懂事啊?”
反要亲戚劝,“他也不是故意的!这东西也不值几个钱!”
像政老爷对贾宝玉发火,也是如此。还是像过年回家,当着亲戚,被问说今年收入如何如何,严父大人不会对亲戚夸口“你们看我家这孩子多有出息”,倒会故作矜持地说“比去年倒是有点进步了!但不能骄傲!”
——其实心里乐开花了。
《红楼梦》里过年时,老太君老祖宗自称“我们这样中等人家”,也是如此。
如果谁读书读死性了,以为贾府真如老太太自称的中等人家,就误会了。
这句实在太妙,梁左先生在《我爱我家》里面有一集,《姑妈从大洋彼岸来》,让以前贵胄后裔胡太太也这么说了遍:
“就是我们这样中等人家,传膳的时候,一道接一道,半个北京城都听得见。”
也是这个自夸劲儿。
于是老傅还特意抢白了一句:
“您这话大点,半个北京城都听得见你们吃饭声?”
按说政老爷也不是故意如此。他行为端方,孝母友弟,被生活磨平了的中年人。少年时多半也风流过,现在(指书里)也不错,是贾府中年人里,相对不油腻的一位。
但也就是这样子,得当个社会规范人,反而无法真情流露。
像后来猜灯谜时,贾政这里简直有点可怜:
贾政亦知贾母之意,撵了自己去后,好让他们姊妹兄弟取乐的。贾政忙陪笑道:“今日原听见老太太这里大设春灯雅谜,故也备了彩礼酒席,特来入会。何疼孙子孙女之心,便不略赐以儿子半点?”
哪怕是至亲之人,大家都不能有话直说,得绕着弯说。
要夸还得先骂,还得由人来铺台阶。
为什么亲子之间,不能有话直说呢?
政老爷为啥不能直接就在大观园里,当着清客,指着宝玉,大声说“我这儿子虽然有些乖张,到底是有才情的,我很欣赏他!我就是想听他题名字,你们稍微配合着点!”
就像,我们都爱父母,但从小到大,很少直接走回家,平白无故直抒胸臆地说一句,“爸妈我爱你们!”
——我有个朋友,有一天忽然这么表达了,爸妈第一反应:“你生什么病了吗孩子?”
当然了,政老爷这种大户人家,规矩重,又有清客凑趣,自有一套委婉的表达方法。我这种人领会不到其中美妙的所在。
只我觉得,亲子之间,能彼此好好说话的,就多把握机会吧——太多人总想着“我以后再跟爸妈表达亲密吧,现在先绷着点”,一不小心,岁月流逝,自己和父母就都忙了、疏了或老了。
最适合作为亲子说话的年头,欻一下,就过去了。